虽然今日“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它仍然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个技术中蕴含的伟大力量,到现在才开始逐渐释放。那么,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究竟是由谁提出的呢?最初的人工智能与今天的人工智能又有哪些区别呢?
人工智能的萌芽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二战结束不久,战争中的很多军用技术蓬勃发展。在战后的美国,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也不断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甚至形成了新的学科。比如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和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信息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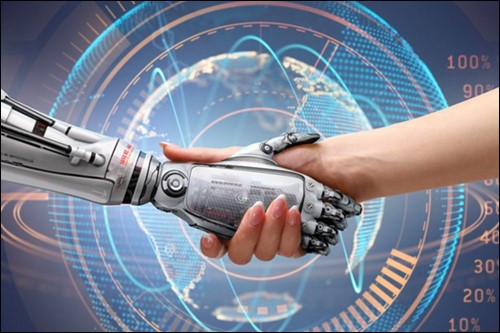
在信息技术萌芽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科学家开始考虑如何用自动决策系统或机械的方法来解释人的决策。1965年,达特茅斯学院的年轻助理教授约翰·麦肯锡(John McCarthy)在他的主场请来了包括香农在内的一些对“能思考的机器”有兴趣的科学家。包括MIT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卡内基工学院(今天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的司马贺(Herbert Simon)等。
在这个会议上,麦肯锡与多位专家激烈讨论,最终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确立为这一门新学科的名称。在几天的讨论中,这些在数学、逻辑学和信息学领域的专家同时也讨论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问题,会议后大家分别回到自己的大学把新的想法吸收创新,不但使其大学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的重镇,也为后来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会的人中还有司马贺的学生纽厄尔(Alan Newell),虽然司马贺是纽厄尔的老师,但他们毕生的合作却是平等的。他们共享了1975年的图灵奖,三年后司马贺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纽厄尔和司马贺代表了人工智能的另一条路线——“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简单地说,就是智能是对符号的操作,后来简称为“符号派”。
他们和当时的数学系主任、第一届图灵奖获得者珀里思(Alan Perlis)一起创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从此,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成为计算机学科的重镇,并一直持续至今。而最初的计算机系,也发展成了美国乃至世界计算机门类最齐全的计算机学院。作者以前访问学习的CMU机器人所(Robotics Institute)就是以两位先驱命名的:Newell-Simon Hall。

明斯基回到麻省理工后创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他与西蒙·派珀特(Simon Papert)发表了《感知器》一书,提到了最早的神经网络模型在解决异或(XOR)问题方面的限制。他指出,神经网络被认为充满潜力,但实际上无法实现人们期望的功能。神经网络的研究迅速陷入了低谷,人工智能进入“暗淡”时期。
20世纪60年代,明斯基又首次提出了“telepresence”(远程介入)这一概念。通过利用微型摄像机、运动传感器等设备,明斯基让人体验到了自己驾驶飞机、在战场上参加战斗、在水下游泳这些现实中未发生的事情,这也为他奠定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倡导者的重要地位。
霍兰德(John Holland)是密歇根大学的计算机学家,他却另辟蹊径,开始研究随机的优化问题并提出了“遗传算法”。因为很多人工智能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转化为优化问题(optimize problem)。而“遗传算法”本身又可以被直接拿来使用到任何问题,只需要定义好“染色体”和适应度函数即可,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即插即用”(Off-the-Shelf)的算法。
霍兰德指导他的学生们完成了多篇有关遗传算法研究的论文。1971年,Hollstien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把遗传算法用于函数优化。霍兰德在1975年出版了《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自适应》(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这是第一本系统论述遗传算法的专著。霍兰德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遗传算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提出了对遗传算法的理论研究和发展极其重要的模式理论(schema theory)。在此基础上有各种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不断产生,很多的期刊和会议也因此诞生,渐渐形成了“进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这个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

壮志雄心与困难重重
达特茅斯会议之后,这些第一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都雄心勃勃。司马贺(Herbert A。 Simon)甚至说:“在1968年之前,计算机就将战胜人类的国际象棋大师。”“在1985年之前,计算机就能够胜任人类的一切工作。”马文·明斯基也预言,“在1973-1978年,就能够制作出一台具有人类平均智力的计算机。”这些充满信心的话让当时的政府和军方非常感兴趣,向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
然而,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们似乎错误地估计了人工智能学科的难度,他们这些充满信心的预言中几乎都未实现。直到1997年,IBM的计算机“深蓝”才成功战胜了人类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到了2016年,人工能“AlphaGo”才战胜人类的围棋冠军。而时至今日,也没有人工智能能够胜任人类的一切工作。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对于这些无法兑现预言的专家非常失望,纷纷减少了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经费投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也陷入的低谷。
尽管发展一个能够胜任人类所有工作的计算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存储能力,让计算机在某一个领域超过普通人的水平是不难实现的。因此,专家系统应运而生。专家系统在设计时能够收集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根据一定的程序,进行计算、分析、预测等功能。

例如,最早的专家系统“Dendral”是在1965年由爱德华·费根鲍姆(Edward Feigenbaum)设计的,“Dendral”是一款应用于化学领域的专家系统,它能够根据光谱的度数分析化合物的可能成分。在人类专家相对匮乏的时代,通过这个系统就能让更多的科学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用于诊断疾病的专家系统,通过专家系统可以弥补人类医生在诊断时可能出现的疏忽。而预测型专家系统能够在综合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背景的情况下预测出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例如对一条河流污染物的迁移扩撒进行预测,从而提前采取有效的措施。
“强人工智能”离我们还有多远?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由于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的普及,机器学习作为一种学习大数据背后的规律的方法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后来深度学习的发展,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希望,当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技术、哲学、伦理上的讨论。
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希望,当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其中讨论重点之一就是目前基于逻辑和计算的智能被称为“弱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是在某一方面能够表现出智能或者说看起来像是智能,而不希望研究出与人类相同的智力和思维。例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方面的人工智能,这些人工智能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图像识别领域和语音识别领域)具有智能。尽管目前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人工智能也具备了自我学习能力,但它们只会在自己的领域中去学习,而不会像人类那样产生自己的好奇心,从而去探索全新领域的内容。

虽然弱人工智能的名字中带有一个“弱”,但实际上,弱人工智能的实力可不容小觑。目前的主流研究都集中于这一类弱人工智能的研究上,且产生了巨大的研究突破。例如能够战胜人类顶尖高手的围棋机器人Alpha Go也是一款“不弱”的人工智能;在千万张人脸中一眼就看到目标人物的人脸识别软件也是弱人工智能;能够自己穿梭于亚马逊物流仓库中并且在电量不足时找到充电桩自动充电的物流机器人,以及能够看清路况自动将人员安全送到目的地的自动驾驶汽车,都是属于弱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且能够最直接的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因此各国对于弱人工智能的研究都投入了巨大的经费。
相对“弱人工智能”的是“强人工智能”。尽管科学家们所希望的就是创造一个具有和人类一样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自己的人格的人工智能,但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的进展,强人工智能还只能存在于科幻与文学作品中,例如《机器姬》里的艾娃,《黑客帝国》中的母体“矩阵”。

强人工智能强调的是计算机需要具有自己的思维,而计算机在获得自己的思维之后,是否还会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体系去思考,对于目前的科学家来说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按照计算机思维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类人思维的人工智能和区别于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例如《超能陆战队》中的大白,就属于前者,尽管外形并不是人类,但它的思维方式与人类一致。而获得了自主思考能力的“矩阵”(《黑客帝国》)和“天网”(《终结者》)系统,它们就属于后者,它们产生了区别于人类的价值观,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去执行“保护人类”这一项任务。
毕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制造一个强人工智能就意味着制造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生命体,这一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也有不少的宗教学者、哲学家反对强人工智能的研究。如果说强人工智能是现代都市里的摩天大楼,那么目前人类在人工智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只能相当于原始人所穴居的洞穴,从当今的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